出品|搜狐科技
作者|汉雨棣
编辑|杨锦
“不说根本看不出来这是县里的购物中心”“老家都有这么大的购物中心了”“为什么县城老家的购物中心越来越多了”……这是近年许多返乡人共同的惊叹。
购物中心拔地而起,玻璃幕墙映着下沉广场的喷泉,各类咖啡、餐厅和快消品类的招牌赫然在列;三四线小城市聚集着多家商业综合体,人流如织不输一线商圈。
看似繁荣的表象下,也有许多危机暗流涌动。地租较高峰时期已经下降30%-50%,餐饮正在代替原本的零售业务,中高端餐饮也正在向低价快餐“让位”。也有从业者告诉搜狐科技,“电商的冲击远大于消费降级。”
低线城市的商业版图正经历一场静默革命。当一线城市购物中心审批收紧时,三四线城市却掀起”造Mall运动”。但繁荣背后,地租下滑、电商冲击、消费降级等问题暗流涌动。这场狂飙从何而来?又将驶向何方?
地租跳水
购物中心的地租相比于最高峰已下降了30%~50%。
陈峰(化名)是一位在购物中心体系内,从事十余年筹备运营工作的资深员工。他告诉搜狐科技,近年来,低线城市的地租相比疫情前整体下降了30%~50%。即使疫情结束后的2023年到现在,地租仍呈现下跌趋势。
这种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,加上疫情后市场经济环境不佳,失业率上升,导致消费力下降。
从商业地产角度来看,在土地财政依赖度超80%的三四线城市,商业综合体成了撬动新区地价的杠杆。
有报道称,现在开业的商超多是2018-2020年拿地的项目,硬着头皮也要开出来,否则土地会被收回。
陈峰也解读称,从拿地到开业,项目周期可能需要三五年。国企可能会继续推进,私企则可能因资金问题而停工。近几年开业的大多是国企央企或大型连锁企业,且多以轻资产运营为主。租金是否会继续下滑,要看房价和生活水平的变化。
而从地区来看,不同地区的地租差异较大,不能简单以县或市来区分。好的县城可能比一些地级市的地租更高。陈峰表示,江阴、昆山等县级市的购物中心发展较好,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受上海辐射,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发达,人口和消费力都较强。
陈峰指出,好的商场可能地租降幅不大,甚至能保持稳定或略有增长,但有些场子可能已经关门歇业。影响大型购物中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经济、人口和地段。
其中,经济方面主要看人均GDP、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;人口方面要考虑区域人口密度;而在地段方面,城市的“新旧”也严重影响购物中心的表现。当前大量三四线城市的老城区呈现出空心化趋势,新城区就成为了成商业主战场。
陈峰同时强调,县级城市的商业发展并非都比地级市差。一些经济发达的县级城市,由于人口密度高、消费能力强,且如果当地购物中心没有强有力的竞品,会比一些地级市的商业环境更好。例如,温州瑞安县作为一个县级市,其五悦广场的地租水平甚至高于一些地级市的购物中心。
也有分析师对搜狐科技表示,一线城市审批购物中心项目越来越少。低线城市的娱乐购物休闲需求崛起,购物中心可以满足这部分需求。就购物中心的发展前景而言,不同城市和区域差别非常大。
生存逻辑已变。过去拼地段”占坑”,现在要靠”算账”——区域人口是否充足?周边住宅入住率能否撑起客流?有无产业提供稳定消费力?算不清这些账的玩家,正被加速淘汰。
电商”绞杀”
现在提起“去逛购物中心”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买东西,更多是为了聚会。
这一印象或可以得到相关数据的佐证。据RET睿意德中国商业研究中心的监测数据,2023年中国消费者到达购物中心的目的,仅有21.6%是为了购买服饰,而10年前的这一数值为67%。
艾媒咨询数据进一步显示:2023年中国居民在商圈逛街时,逗留时长通常为1—2小时(59.1%),人们前往商圈多为无目的性的闲逛(66.4%),其次则是聚会(58.8%)。
这样的转变并不是近些年的事情,陈峰直言,“电商的冲击比经济形势影响大。”
陈峰表示,电商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,购物中心的零售业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,零售品牌减少,购物中心的零售呈现出连锁化的趋势,个体商户一般不愿意进入购物中心。
“十来年前有电商之后,百货就已经慢慢不做了,逐渐变成购物中心。大家去购物中心逛逛店的话,很多不是目的性的,而是随机性的消费。购物中心相对于百货零售,品牌性还会比较好,随机性消费比较高。”
“电商这个后来又出了这种不同的类型的电商,疫情把大家关在家里的消费习惯变化了,又有直播啦,那这个再加上经济。现在零售品牌越来越少了。”
电商的致命一击早已埋下伏笔。连锁品牌撤退潮蔓延,Zara、H&M等快时尚巨头关闭低线城市门店,耐克、阿迪达斯转向”大店模式”,县域市场仅保留核心商圈店铺。
当零售溃败,餐饮与体验业态成了救命稻草。深圳万象城这一高端商场,在四楼开设了美食广场。这场转型代价巨大。餐饮区坪效通常不足零售的1/3,且装修补贴、租金减免已成招商常态。但别无选择——”总比空着强”。
当零售的功能被取代,餐饮、娱乐等体验式的“情绪消费”已经成为了购物中心的核心。太原吾悦广场建造了首个太原城市上空流转的摩天轮“太原之眼”,还推出摩天轮+餐饮、摩天轮+KTV、摩天轮+潮酷PARTY、摩天轮+情感活动等体验。
谁能抓住”清醒的消费者”?
与供给侧的萧条相比,需求侧”该省省该花花”的哲学,则更加注重性价比。
蜜雪冰城在县城把价格打到4元一杯柠檬水,仍要面对本地品牌的”3元狙击”;餐饮区”9.9元套餐”广告铺天盖地。社区超市开辟”临期食品专区”,3折价的奥利奥被抢购一空。
餐饮也受到了影响。陈峰分析称,客单价下降,好多中大型的餐饮都开不下去,反而快餐小餐还可以。很多购物中心的连锁餐饮,特别是200~400元之间的餐饮店就遭遇了较大的困难。
与此同时,许多新业态的消费也正在席卷。但是陈峰也指出,三四线城市难以自产出新的业态,大多数是从一线城市“复制”来的。
新的情绪消费崛起,各类“谷子”店、二次元主题馆里,学生党为限量手办一掷千金;成都COSMO用赛博朋克风吸引潮人,艺术展、快闪店、livehouse成标配;山姆代购在县城养活数百中间商,河南胖东来用”西瓜标糖度、鱼缸标PH值”的变态服务横扫低线市场。
在谈到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时,陈峰认为,电商的影响力将继续扩大,而实体商业将更多地依赖于体验式消费和品牌连锁店。
三四线购物中心的崛起,是中国城镇化与消费分级碰撞的魔幻产物。这里有政府造城的雄心、开发商赌命的疯狂,也有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。
当泡沫逐渐退去,真正的赢家或许是那些”算清账”的人——他们知道县城不需要第二个万达,但一定需要热气腾腾的火锅、孩子尖叫的游乐场,以及一份触手可及的”精致生活”幻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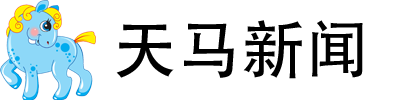
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





